首页 -> 2008年第5期
“向党交心”资料披露一段往事
作者:姜东平
字体: 【大 中 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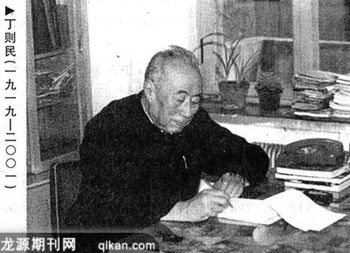
“民主”教育
由于长期受到美国式的“民主”教育,回国之初,在思想观念上,与新社会的语境格格不入。丁则民写道:“常听弟、妹、侄女(都是党团员)称美国为美帝国主义,而且把它说成是纸老虎,觉得不大顺耳。当时虽未表示异议,心里却不以为然,因为我想到,欧美各国敌对政党竞选时,竞选人尚称对方为先生,而我们为何称美国为美帝国主义呢?这不是表示我们的度量太小了吗?为了宣传和教育人民的目的,说美帝国主义是个纸老虎尚可,但我国真是采取这样轻敌的态度,那么将来定要吃亏的。”
对国内到处悬挂毛主席像,他感到很不习惯。“我完全不理解劳动人民和党的血肉关系,也根本不能体会他们尊敬和爱护革命领袖的情感,因而把各处悬挂毛主席像一事看成是偶像崇拜,并且怀疑:这种现象不是和独裁国家盲目崇拜领袖的风气一样吗?”
1950年,丁则民入“革大”(即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学习。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经常参加学员们的小组会议,被称为“干部下组”。每至干部下组,小组空气便紧张起来,气氛沉闷,场面尴尬。丁当时认为干部下组表面上是帮助大家学习,实际上是起着“监督”大家的作用。对中共所提倡的“民主集中制”也产生困惑和不解,“错误地认为民主集中制是变相的独裁。”丁则民曾向下组干部提过这样的问题:“假设领袖违反人民的利益,走上了错误的道路,像铁托在南斯拉夫那种情况,怎么办?怎样来纠正?”意思就是说,在民主集中制的情况下,领袖权力过大,因而不可能防止领袖的叛变,领袖违反人民利益时,也没什么办法进行纠正。嗣后,中国所发生的事件表明,丁先生的担忧并不是毫无根据的。
当丁从北师大调到东北师大以后,他才发现,东北师大对于“民主集中制”的施行,却远不如北师大好。这种感觉与从北京来的同行们的普遍印象相吻合。
——北京高等学校内,对领导提意见的风气较盛,领导亦较重视群众的意见,而且不追究提意见人的思想;东北师大领导不大喜欢倾听群众的意见,尤其是不同的意见,而且常有追究提意见者思想的倾向。因此,有些人不愿意提意见,怕找麻烦。
——北京高等学校领导的自我批评精神较好,常在工作检查中进行自我批评;东北师大领导缺乏自我批评精神,成(仿吾)校长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报告中,还是着重地批评了教师,而对自己的工作则很少检查。
——北京高等学校领导常召集有代表性的教师开座谈会,交换意见;而东北师大领导很少召集这样的会,很少和教师谈心。校党组织喜欢说正面话的人,重视和信任这样的同志,而不大喜欢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对他们信任较差。
——东北师大缺少“大胆怀疑,追求真理”的风气,领导也很少倡导、鼓励这种风气。因此各级会议中,很少有争论,尤其是有益于工作的争论,由于缺少这种风气,有些人不大敢发表与领导不同的意见,有些人尽说些符合领导意图的话,但不大像是由衷之言(事实上这种情况真到现在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作者注)。
在教授世界史的问题上,丁则民曾与一位年轻同事发生矛盾。此前,他在教学上曾经给予这位同事热情帮助,然而这位同事在讲课之后,却骄傲起来,并刻意在政治和思想上与老教师们“划清界线”,认为老教师思想落后,一无是处,不再把老教师放在眼里。丁感到老教师们受气,认为不能在一起合作共事,与党总支缺乏民主作风、偏袒青年教师有直接关系。
由此而对东北师大的党组织有看法,感到东北师大党不如北京的党。认为“这是因为北京有旧民主传统,东北受敌伪统治,没有旧民主习惯,服从心重,不协商也可行得通”。
“高知”入党
1954年,丁则民与丁则良谈论到党对科学文化领导的问题,认为当时党员科学家人数少,党对科学文化的领导较弱。丁则良说:党对科学文化的领导只有两种办法:一是迅速培养党员科学家,扩大党员科学家的力量;一是某些旧知识分子入党,加强党在科学文化界的领导力量。当时丁则民对他的看法表示赞同。
1955年之后,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中包括早年加入同盟会并参加辛亥革命的中央戏剧学院院长刘仙洲,北京农大副校长沈其益,北大数学系副主任程民德,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艾中信、古脊椎动物研究所所长杨钟健等。到1956年,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公布后,全国各科学机关、高等学校旧知识分子入党的更加多了起来,形成风气。入党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同时并不排除一些投机的想法:入了党,等于进了“保险箱”,可以免受政治风浪的冲击,为自身的前程积累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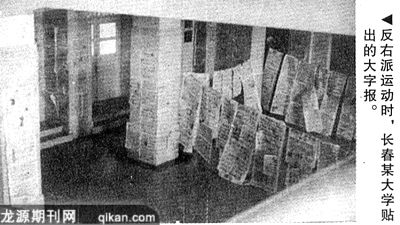
在东北师大,丁则民身边“表现突出”的同事亦迈进党组织门槛。对此,丁则民认为这是党为了加强对科学文化领导,而放宽了标准,“在被吸收入党的高级知识分子中,主要是因为他们历史清白,平常听党话(即顺着党的意图说话),而他们思想觉悟并不一定高,也不一定都达到了党员水平,只是由于他们赶上了浪头,而被吸收了。特别是对那些表现出政治上优越感的新党员(指高级知识分子的新党员),更是反感”。从这种认识出发,丁的情绪很是悲观,包括自己在内,多数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必须经受长期的考验,不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入党是极其困难的。“凡是历史上有污点(如参加过反动党团,或为反动派工作过)的人,尽管他们的政治觉悟提高很快,也很难被吸收入党。”
国际事件
1955年,苏南关系恢复正常化时,苏联领导人曾说,1948年苏南关系到之被破坏,系由于根据被捏造的情报——即贝利亚叛国集团捏造的情报的结果。
丁则民置疑这种提法。“捏造之情报”,能起这样大的作用?那么“根据捏造的情报而作出错误决定的苏联领导机构不负任何责任吗?是否有将过去苏南关系被破坏的各种因素都完全归咎于贝利亚叛国集团的倾向?苏共中央对待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没有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认真检查,完全把这种关系被破坏的责任归咎于贝利亚叛国集团,是不够实事求是的。”
“假设苏南关系之被破坏,系由于根据被捏造的情报的结果,那么1948年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是否也由于根据被捏造的情报而作出的呢?参加情报局的还有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难道它们都不掌握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情况的正确情报吗?为什么会议会仅仅根据贝利亚叛国集团所捏造的情报呢?并据此而作出错误的决议呢?”
波兹南事件发生后,波兰统一工人党领袖哥穆尔卡曾指出:酿成这一事件悲剧的因素应该从党和国家的政策、措施中去寻找,而那些把这一事件说成是帝国主义特务和挑衅闹出来的说法,在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
丁则民认为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因为“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单纯强调外因而忽略内因,那就难于检查出波兰本身存在的错误和问题,难于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因而也就难于保证这种事件不再发生”。“帝国主义特务的破坏、挑衅活动的威胁,对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都是存在的。为什么只在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原因首先应从内部找。对于匈牙利事件的产生,拉克西——格罗集团推行的反人民政策是主要的,而纳吉政府的叛变更是使事件发展到不可收拾局面的主因”。
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后,丁则民曾阅读了《美国工人日报》转载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当时他在思想上产生了很大波动和疑问。对斯大林这样“伟大的历史人物”也会犯这样严重的错误感到吃惊,感到“不可思议”,“政治也确是难以捉摸”。斯大林所犯的“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严重错误是骇人听闻的,“他的错误给苏联造成的损失也是极其严重的。为什么不能于他在世时进行批判、纠正呢?而是在他逝世后才提出对他的批判呢?”他认为,把一切严重的责任都归咎于斯大林个人,或者把过去的一切功绩都归诸于他个人,同样是错误的。